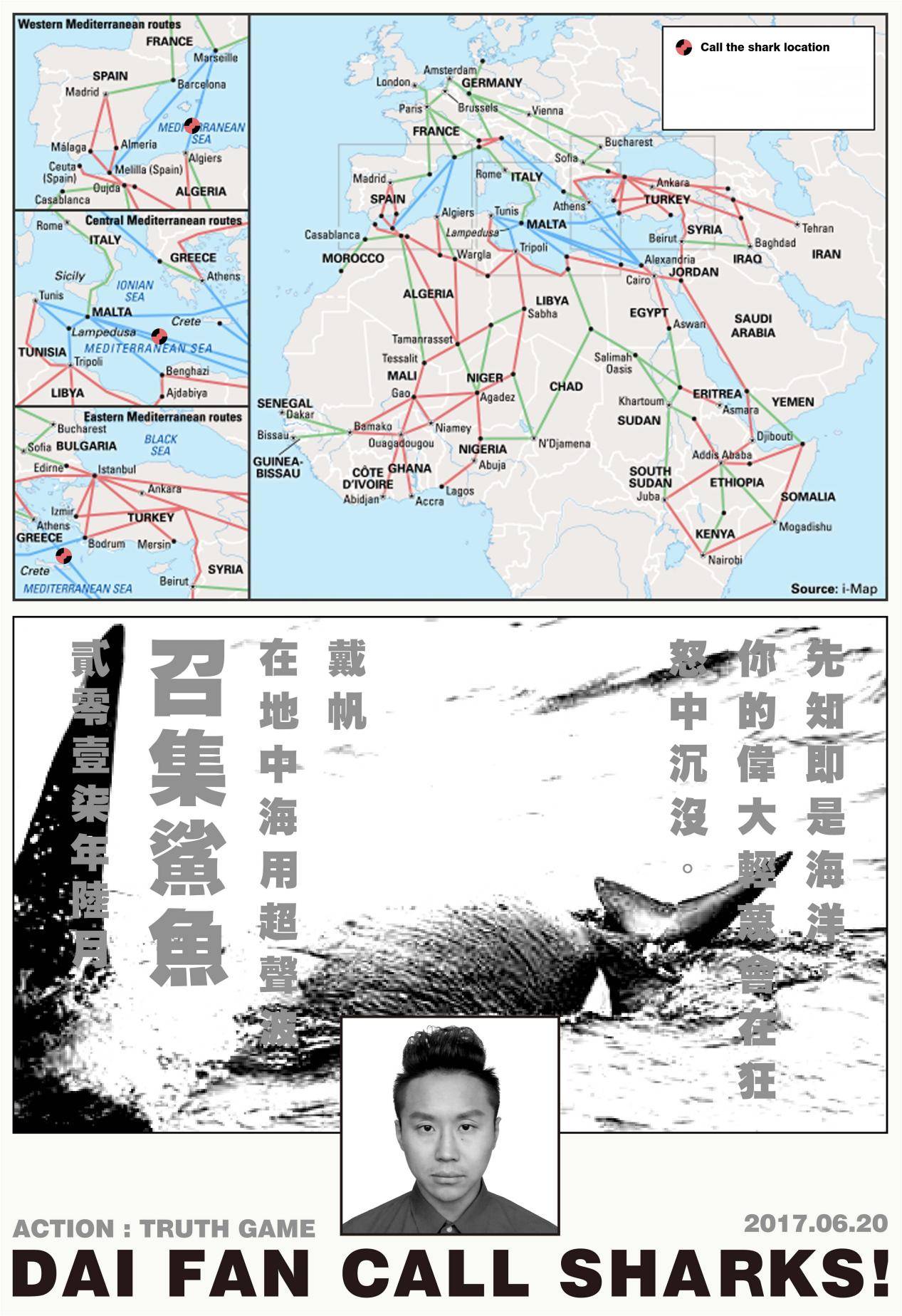天才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颠覆正常的世界观,在绝望之巅挣扎,燃起超脱生死的激情,死亡、上帝、无限、时间、永恒、历史 真理、伦理等宏大的哲学命题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在如火山中喷发的火焰生命中获得了有机的现实感。天才是文明的对立;每一个真正的天才或智者,无不经历过对人类深深的厌恶。但是,他们最后却成为了人类最大的启蒙者。天才改变了事物的性质;它的特点扩及它所接触的一切事物,它的光辉超越了过去和一切,照耀着将来;它走在这世纪的前面,世纪跟不上他的步伐。

正文 :
设计之都:戴帆先生,你在国际上荣获亚洲设计大奖、环球设计大奖等几十个顶级奖项,被誉为是当今设计界的“设计鬼才”,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称谓的,“鬼”在哪里?
你提到“鬼”,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夏天的晚上,我躺着外婆的膝盖上望着星空,外婆给我讲鬼故事,每次我在外婆的有点恐惧感又甜蜜的鬼故事中慢慢睡着了,进入梦中。童年时,我开始梦想着一种设计,这种设计不会努力地去构建某种意义,而是给某种事物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微风飘过的声音,在荡漾的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无意中带来了新的感觉,去召唤这些已凸显的感觉,把它们从远古的沉睡中唤醒,迸发出想象的火花,携带着风暴和闪电……
设计之都:您的设计不仅充满了前卫,与此同时充斥着尖锐、富有挑衅,这背后您想传达什么设计思想?
我先粗略的谈一下我的一个空间作品“21G”的一个具体概念,这是一个麦克杜格尔的灵魂称量实验,麦克杜格尔制造了一架精密天平:一张吊在一架支座上的床,测量床及床上物体的总重量,素质可以精确到5克。1901年4月10日17点30分的时候,第一位垂死者被麦克杜格尔放上了他的灵魂天平。3小时40分钟后,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后的重量与他之前的重量差异是21克。这个实验描绘了让人迷惑的图景,灵魂重21克。医生认为,灵魂是有重量的。欧洲中世纪的一位医学家圣多里奥(Sanctorius)在在圣多里奥(Sanctorius)的房子里,他是量化实验医学的鼻祖,30年间一直在一切都悬于秤上的空间中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悬于秤上的他生活的空间包括床、工作台、椅子,他以此记录自身身体体重的点滴变化,从所进食物的重量,到所排泄的废物的重量,他都称量记录。我的空间为自己的思想准备了一个能在其中冒险的迷宫,在这里我打开了禁锢的铁闸,我的空间是一个特殊知识领域的剖析,是尝试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人们所习惯的空间的批判与质疑。我不想去探寻连续性和系列性,而是力图分析每个空间的特殊性和差异。




设计之都:你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什么促使你往设计这个行业走的?并且跨界多个领域,却能做得如此出彩?
任何值得去学习的东西都是不可教的,试图通过教育去获得某种东西是一种对自己不诚实的体现。人应该凭着他自己。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人必须要通过教育去开始工作,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绝大部分的现代教育不是在激发人的创造力,而是在培养一个为社会机器运转的零件。教育总是用过去的标准衡量现在,同时,用过去的标准在构建现在,如果设计师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中,其产生的只能使过去的设计。一种新的事物,当它被人们无意识地依据已认可的形式来衡量时,却总会显得是对作品只有把往昔留在身后并预告未来时,才能留存下来。最好的教育就是对教育的不服从。学校和医院、监狱、公司一样,都是管制、规训人的场所。我中学时成绩在年级里一直都是前几名,但是我的好朋友都是那些成绩不好,不喜欢读书还敢于和老师叫板和抗争的坏学生,我欣赏他们他们迷乱的经历和放纵生活那种不管不顾的状态,他们是越轨者,质疑了教育的界限,破坏秩序,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不受阻挠地摆脱限制,他们或者因为学古惑仔打架被开除,或者因为玩恶作剧破坏学校秩序中途退学,或者逃课、打游戏、恋爱拿不到毕业证。不服从教育的同学在我眼里才算拥有属于自己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因为追求更多自由与扩张自我意识而充满了温度和能量,青春不再仅仅是一个恣意妄为随意越界的生命的脉动和欲望,而是一种激烈的现实性。
设计之都:水这个元素在你所创造的建筑中,似乎具有非凡的地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这个元素并不算新颖,也不特别,你是怎么将它做成独一无二的?
只能谈谈我对水感觉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片段……水在水中……轻盈的水,深邃的水,灵玄的水,沉睡的水,纯洁的水,狂暴的水;在清晨的池塘中的水给人一种特别的恐怖,给人一种更明确的潆绕,天亮时,水面的烟雾还未散去,幽灵在湖面游荡,在阳光出来之前,幽灵消逝了,水中的幽灵密集起来;水的性使人联想起躶体的女孩,水多么明亮,会多么真切的反照出最美丽的形象,在水里沐浴的女孩年轻而又羞涩,内心并不总是惶惶不安,水使人联想到自然的裸露,那种保持纯真无邪的裸露,如同羞涩的水草悠悠的飘在在鱼吐出的气泡漩涡之中,在水中出来的生灵是一种逐渐变得物质化的倒影,随着涟漪将意识传递到山的那一边,水的结构中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水的时间不是直线的、历史的,而是循环的、神圣的、永恒的。水是神话的延伸,水的仪式与神话紧密相连的;神话属观念层面,而水属动作层面,水与神话互为表里。水是承载建筑潜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诸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禁忌、时空观等都汇集在水之中。静观水,水就是流逝,就是消融,就是死亡;坎坷、变故变成了语言总是被水的幽闭、孤傲,以及浩美所牵引。思绪有时面对着清澈的水,整个水面是一片辽阔的倒影,幽晦而神秘,总是被卷入……一种最令人着迷的意识深处之中,其卷入程度之深,往往使视界……发生扭曲,产生出接近谵妄的想像……思念在忧郁而阴沉的水之中,在传来古怪而阴森的耳语的水中,在辽阔的柔软的水面上,做着无尽的梦……
设计之都:你如此的设计天赋和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吗?设计师是一个独特的行业,你觉得天赋和努力哪个重要,你的天赋在你的现在的成就中占了多少?
我非常幸运的是从小父母从不阻拦我做任何决定和尝试,设计和艺术和音乐一样都必须遵循极端严格的训练和技巧,小时候父母给我提供了这样的环境。衡量天赋的最重要的一个尺度就是敏锐度,并不仅仅是感觉器官的敏锐性,而是大脑在察觉事物方面的敏锐性,顶尖的设计师就是那种禀赋更复杂,更丰富,更多样,更深刻,更细腻,更强烈的人。
设计之都:有没有什么文化或理念是影响你最深刻的?
我出生在长沙,在湖南,一种来自远古的具有强烈的狂热的社会情感的的宗祝文化,并未随着时代的进程而退色,这种混沌的情绪反映,由于其古老会像经验似的时代积累下来,沉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成为历史在心灵中的投影,并影响到一个我们那个地域的心理结构。我的许多作品不但反理性,而且是反人本主义的,而这两者正是现代主义的根基,通过个体的行动去敲击并撼动整个现代历史,设计和艺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连接有形与无形。使观众经历一种极限经验、一种精神启蒙,如参加宗教祭典一般,这种经验不能重复。设计和艺术应超越现实,超越社会冲突,它有更“崇高而隐密”的目标。楚人雕刻作品的实有体量并不大,但是楚人智慧之处在于以特殊的处理方法,比如“鹿角的张扬”、“凤鸟的引颈向上”等暗示出一个庞大的心理空间。重要的是具有现代人所无法袒露的,只有人类童年时期才具备的那种异常纯真的感觉。这种空间感觉已经远离我们,但作为“人类永不复返”的阶段,并将激荡我们当下心灵中潜藏的原始的天真,以及与万物沟通狂放而奇诡,敏感而细腻的气息。
设计之都:我们知道你有一个震撼人心的未来酷刑系列作品,对人具备真实的惩罚和攻击性,拥有华丽、夸张的外表色泽和精巧、繁复的造型设计,却仍杀机四伏、凶险万分,不理解的看客第一反应是这个设计师是否心灵阴暗,在这个作品背后你想要真实表达的是什么?
残酷不是目的,要表现潜藏在人心中,最原始的、不经文明矫饰的欲望与人性,必然脱不了凶残和暴力。当时,展览中的入口处是一件名为“凌迟”的作品,红色的金属不锈钢机器是一种机械自动化运转的“凌迟”功能的机器,这个机器本身具备高科技和科幻宇宙的精致漂亮美学风格,机器上的刀子将人身体上的肉切割下来。在中国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120刀,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远远超过了前代。凌迟从文化史的意义上来看,酷刑及其它残忍行为的状况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中国的某种落后导致了它的前卫,酷刑的进化暗示了原始、野蛮的文化形态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之间的冲突与悖论。还有一件作品是“五马分尸”:五架金色的金属材质的战斗机,将固定在中间五角星的金属板上的人往五个不同方向向外拉断身体,“五马分尸”既是虚构的作品,又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人类酷刑的方式是由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和权力结构决定的,通过华丽、精致、愉悦的视觉感官与现实、血腥、残酷功能之间爆裂的冲突,展现了人类历史变化中扭曲的人性,显现出历史刑罚的合法性与中国进化论的无奈何窘境。亚里斯多德以悲剧所引起的“恐惧”与“怜悯”,达到净化观众心灵的目的。残酷既是生命的真义,艺术就应使观众意识到生命的残酷。所以“残酷”,就是自觉,是一种清明的意识。现在大量流行的小清新、甜蜜的作品不能引导人自觉,而只能给人一种逃避。一般人听到残酷,立刻想到的是血腥和暴力,其实世界对人来说,是残酷而无意义的。人无论如何躲避,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诅咒,这种宇宙间不可逃避的天罗地网,这就是残酷。